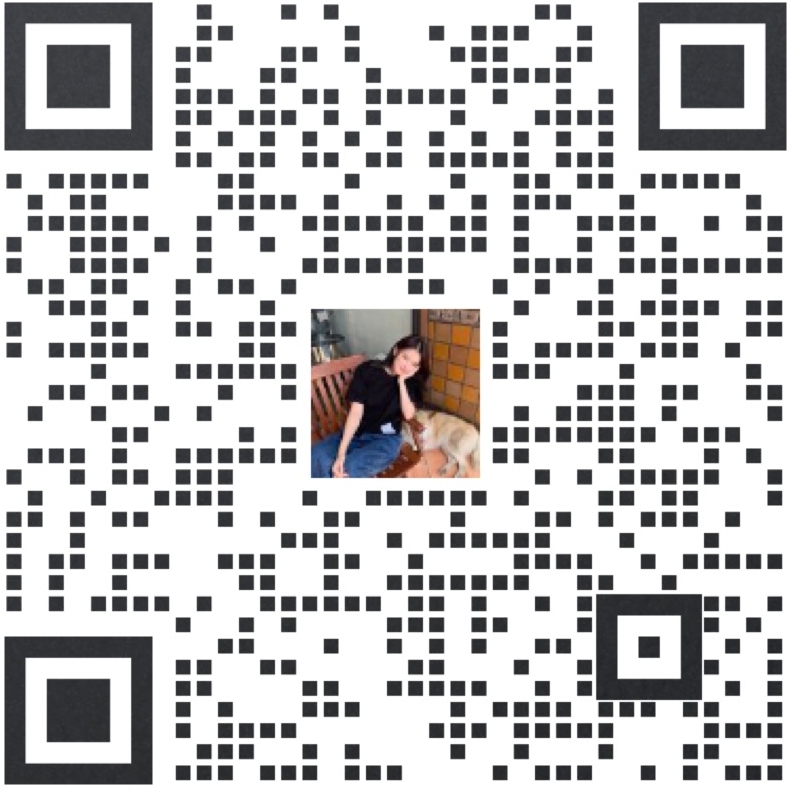精子捐献为无数患有难言之隐的家庭提供了纯净的解决方案:当某个人或某对夫妇想要一个孩子,并且需要外力介入时,拥有充满活力的精子的男人就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个过程看起来像是建立完整家庭的无缝方式,对很多人来说也确实如此。这就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精子捐献为何如此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段时期,精子捐献逐渐从小众实践变成了成千上万新生儿诞生的主流技术。在2010年,也就是有可靠数据可查的那一年,大约有3万到6万名出生在美国的婴儿是通过捐赠精子受孕的,当年大约有400万名美国婴儿出生。
尽管如此,像精子捐献这样简单的交易似乎也是有压力的,而且由于辅助生殖技术是相对新的、快速发展的领域,精子捐献参与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社会和情感挑战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未知的。目前,有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捐精:一是准父母可以用朋友、熟人或家庭成员的精子样本,这通常被称为“已知或直接捐赠”;二是通过精子银行或生育诊所安排的(通常需经过严格审查)陌生人精子。
即使几十年后,精子捐献行为已经变得相当常见,而且其错综复杂在理论上也可理解,许多选择捐精的人仍然对它所能形成的方式感到惊讶。在某些情况下,它会使人感到紧张。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会增强家庭活力。其中让人感到惊讶的一个群体是由不育的男性组成的。
洛杉矶的婚姻与家庭治疗师亚伦·巴克沃特(Aaron Buckwalter)花了15年时间,专门研究生育挑战以及他所谓的“男性问题”。他的工作通常包括帮助男性在不育背景下应对传统男子气概所带来的文化期望。巴克沃特说,理解不孕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承认其中蕴含的悲伤和损失。
他解释称:“你经常会遇到你认为自己会拥有的东西,并且认为你可以很容易地拥有它们。你必须接受自己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巴克沃特经常发现,在异性恋关系中,很难受孕的男性伴侣更有可能在整个过程中感到“紧张不安”:他倾向于治疗的男性“将其视为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或需要搞清楚的阴谋。我们必须赢得胜利。”
巴克沃特表示:“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尽管建立家庭、建立亲密关系、建立联系才是真正目标。只要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在另一端获得奖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直到事情结束后,他们才会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某种情感上的理解。而到那个时候,如果他们无法或不愿意去处理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这会损害他们与配偶的关系,最终影响他们对孩子的依恋。”
当巴克沃特专门为考虑如何应对不孕的异性恋夫妇提供咨询服务时,他发现,与考虑卵子捐赠的女性伴侣相比,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情感上,男性伴侣更容易陷入所有权困扰中,产生“孩子是我的”想法。这些人经常纠结于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巴克沃特说:“对很多男人来说,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往往深陷困扰难以自拔。”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女性伴侣在怀孕期间与孩子有生物学上的联系。巴克沃特还提到了一种“原始的嫉妒”,即当男人不能生育时,这种嫉妒就会产生,这是基于对另一个男人可能导致伴侣怀孕威胁的进化反应。这似乎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因此,巴克沃特说,许多男人不得不努力摆脱它,自我安慰道:“哦,我是尼安德特人,我不应该这样想。”
在许多情况下,捐精-受精的过程都很顺利。对许多家庭来说,捐精是个奇迹,而不是折磨。但是巴克沃特说,应该鼓励男性承认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感受到的任何焦虑、痛苦或羞愧。他补充说:“我希望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人们在不去见治疗师的情况下感受到这一点。但我的希望是,人们应该反思:捐精过程不仅仅是一次交易。”
与我交谈过的一个家庭直接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的故事围绕着两兄弟,他们的家人不愿透露姓名,因为他们的处境很敏感。捐精的哥哥和受赠的弟弟现在都40多岁了,他们从来都不是最亲密的兄弟。在英国长大的他们经常因为争夺玩具和领地而发生混战。成年后,他们仍然在暗中较量谁的事业更成功,谁的婚礼更优雅,谁在家庭能在槌球游戏中获胜。
因此,10年前,当弟弟前往美国拜访哥哥,请其捐出精子以便他和妻子组建完整家庭时,哥哥最出显得有些犹豫。经过几年的努力,弟弟及其妻子发现他们无法有自己的孩子。哥哥记得弟弟在桌子边哭,他向兄嫂解释说,他的身体根本没有产生精子。哥哥回忆道:
“这让我感到害怕,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但在和妻子商量之后,他们同意捐赠。他们推断,也许哥哥帮助唯一的兄弟组建完整家庭会让他们更亲密。
他们的一次授精尝试显示,这种受孕是可行的。哥哥现在表示:“当时我们都非常乐观,认为事情会有好结果。”他的妻子称:“我认为,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事情就开始失控了。”在侄女出生几天后,哥哥和嫂子首次去看望他们。这位伯母还记得自己不受欢迎、令人感到不安的体验,因为新父母不希望他们去看自己的孩子。
这位嫂子称,有一次,在一个安静的时刻,弟弟悲伤地说,他希望能和妻子像普通人那样有自己的孩子。哥哥回忆说,在那次拜访的另一个场合,弟弟冲他和妻子大吼大叫,然后突然冲出会场。这对夫妇回到了美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与弟弟的接触越来越少。哥哥称,任何交流都变得“非常正式”,他觉得捐精毁了他的家庭。?
几个月后,嫂子从一位生殖专家那里得知,这是受助者父亲天性的普遍反应。这位专家怀疑,捐赠者的兄弟感觉受到了威胁,就好像这次访问代表了捐精者的突袭,仿佛新生儿是他的孩子一样。这位嫂子称:“我就想:‘天哪,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一件大事,它将考验你们关系的极限?包括在捐精银行工作的医生,没有任何人说过:‘嘿,坐下来。想想这段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偶尔,有这种信息的故事会出现在咨询专栏和支持网络论坛上,但总的来说,它们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丽莎·乔罗登科(Lisa Cholodenko)的电影《孩子们都很好》(The Kids Are All Right)讲述了两个女同性恋的孩子寻找捐精者时发生的家庭剧变,这是捐精领域为数不多的虚构探索之一。
此外,心理治疗师金伯利·克鲁格-贝尔(Kimberly Kluger-Bell)撰写的一本儿童读物《豌豆即我》(The Pea That Was Me)也讲述了一个精子捐献的故事,该书因其处理精子捐献情感的方式而受到父母和心理学家的称赞。在书中,克鲁格-贝尔解释了捐精的过程:把精子(男士豌豆)加上卵子(女士豌豆)相结合,让它在女性身体内长成小豌豆。然而,当男人的精子不起作用时,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可以帮助夫妇找到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来分享他的精子,并提供帮助。
出于许多原因,目前还没有监管精子捐献行为的法律。在美国,各州的法律都有所不同。正如乔治敦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概念·辅助生殖技术发展法律和政策》(Legal concepts: the evolution Law and Policy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的合著者苏珊·克罗金(Susan Crockin)所说,大多数州对精子捐赠行为只有基本规定。
大多数州支持《统一亲子关系法案》(Uniform Parentage Act),该法案规定,当一名男子向自愿接受的已婚夫妇捐献精子时,捐献者不是孩子的父母;父权属于怀孕妇女的丈夫。而在没有完全采用同样法律的州,精子捐献者理论上可以声称自己有孩子的监护权,或者被要求支付子女抚养费。
2017年,考虑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通过《统一亲子关系法案》的两个州颁布了一项更新,只要双方同意,无论男女,精子接受者的配偶都可以成为合法的共同父母。关于如何完善精子捐赠过程,业内还存在很多分歧,尽管专家们对人们应该如何去做有了些清晰的理解。
在美国,最接近监管机构监督精子捐献的是一个名为“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非营利组织。ASRM拟定有成套的建议,医生、生育专家和精子库都可以遵循。ASRM对有些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比如是否要告诉捐赠者的孩子他们的起源(“强烈鼓励”),以及向孩子透露多少有关匿名捐精者的信息。后者正在继续研究中,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允许捐赠者后代获取关于捐赠者的非识别信息。
ASRM还建议,为降低意外出现乱伦的风险,在80万人口内,每个捐献者最多只能生育25个孩子。在许多其他国家,有法律规定,在一定规模的人口中,每个捐赠者的生育数量必须有上限,但美国没有这样的法律。ASRM还建议,在受孕之前,医生应该为任何参与精子捐献的人提供心理咨询,并明确规定“那些选择参与家庭内部捐赠项目的人应该准备好花费更多的时间为参与者提供咨询,并确保他们已经做出了自由、知情的决定。”?
根据ASRM的规定,这些协商应该在捐赠过程开始之前进行,不应该仓促进行,而且应该包括准父母、捐赠者、代孕者以及他们的伴侣和孩子在场。ASRM甚至建议,这些磋商应重点关注“参与者将如何应对未来孩子的独特安排”,并提醒参与者“许多专业人员参与,包括医生、护士、辅导人员,并应该期待接受全面评估。”
专家的出现可以让人们进行重要的对话,否则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对话。安德里亚·布雷弗曼(Andrea Braverman)是托马斯·杰斐逊大学(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妇产科、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学的临床教授,她经常在精子捐赠过程之前(有时是之后)为夫妇提供咨询。对于非匿名捐赠,她会见了捐赠者和他们的伴侣,接受者及其伴侣,然后集合所有人共同讨论“角色期望”,以及“这些信息将如何处理:是否与孩子共享其身世之谜?何时分享?她说,即使是一个小时的一次性会议也会有所不同。
布雷弗曼还要求每个人都讨论一种可能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告诉别人,尤其是在已知捐赠者的情况下,人们肯定会说:“我们关系很好,为何要安排我们去见那个人?’”另外,有些人已经为不得不走这条路而感到难过或羞愧,咨询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在被审视或评判。布雷弗曼称:“坦白地说,我认为这是为什么许多捐赠和许多医生未被认可的原因,因为他们受到了阻碍。”
咨询师将病人转介给律师的情况并不少见,尽管对于这种做法是否审慎还存在分歧。乔治敦大学教授苏珊·克罗金说:“很多人说,如果是家庭捐精的情况,家庭成员彼此相爱,不需要单独聘请律师。”然而,克罗金认为律师可以帮助家庭处理好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尤其是那些他们可能不想考虑的情况。
克罗金解释称:“律师的工作是为当事人辩护,问他们:‘你确定吗,你希望这是个永远无限的捐赠?亦或是你想要说改变主意了,想要回自己的精子,因为你现在恰好是不育的?’”当然,咨询不能神奇地把每个家庭的情况都变成健康环境。与专业的第三方调解人交谈几小时可以帮助解决许多人际关系问题,甚至可能是大多数问题。但是有些家庭,比如那些有着根深蒂固、性格不相容的人,或者有很长一段感情不稳定历史的人,可能不适合进行家庭内部精子捐献。
并不是所有的精子捐献都需要专业的干预才能获得成功和快乐。这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教师丽贝卡·赫尔格森(Rebecca Helgerson)告诉她的朋友们的,她想通过他们的捐献要个孩子。自从她的女儿出生五年来,她发现了一套有效而公平的基本规则。她说:“我希望这是一种舒适的关系,我们彼此了解,但没有任何结婚期望。我们都认识对方,有时候会待在一起。但是我想要清楚地知道谁是孩子的父母,谁不是。我对任何形式的正式关系都不感兴趣,他也不感兴趣。”
今天,赫尔格森、她的女儿、赫尔格森的伴侣、捐赠者以及捐赠者的女性伴侣每年都一起去度假。他们这群人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发生在机场的安检门前。赫尔格森说,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的工作人员总是搞不清应该把哪些成年人和孩子放在一起。不过,有些专家,比如克罗金认为,参与捐献的所有各方都应该采取更广泛的预防措施,法律也是如此。
在克罗金看来,如果你去看医生,说你从亲戚那里获得捐赠的精子时,那么应该遵循所有标准的建议,每个捐赠者和接受者,夫妻或独立各方,至少应该参加心理教育咨询会议。但从法律上讲,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不要求捐赠者和受赠者参与咨询,也不要求生育诊所或精子库遵守美国生殖医学会(ASRM)的建议咨询指南。
至于美国精子捐献的未来,克罗金希望借鉴英国“非常全面的监管”。2008年,就在那对英国兄弟开始在美国稀少的精子捐赠地图上寻找机会的时候,英国通过了《人类受精与胚胎法案》(HFEA),该法案建立了全国性的管理机构,监督所有精子捐献和其他辅助生殖技术。这项法律要求捐精者、受赠者和他们的伴侣事先接受咨询,毕竟这很可能改变了这两个家庭的生活。
关注【深圳科普】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
回复【最新活动】,了解近期科普活动
回复【科普行】,了解最新深圳科普行活动
回复【研学营】,了解最新科普研学营
回复【科普课堂】,了解最新科普课堂
回复【科普书籍】,了解最新科普书籍
回复【团体定制】,了解最新团体定制活动
回复【科普基地】,了解深圳科普基地详情
回复【观鸟知识】,学习观鸟相关科普知识
回复【人工智能】,了解更多人工智能活动详情



- 参加最新科普活动
- 认识科普小朋友
- 成为科学小记者
 会员登录
会员登录
















 深圳市宝安区国际会展中心20号馆
深圳市宝安区国际会展中心20号馆